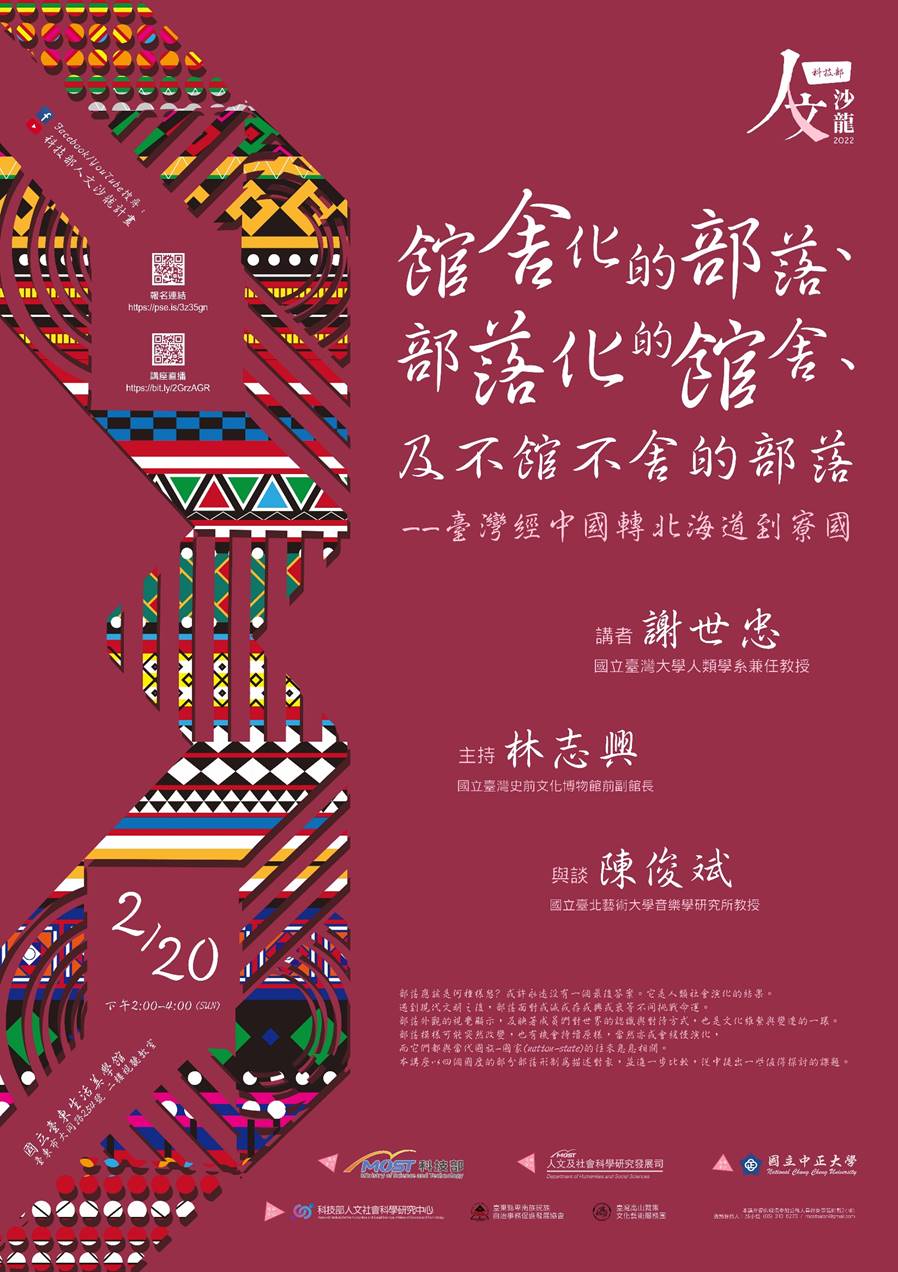|
第56場 |
||
|
日期:2022-02-20 講者姓名:謝世忠 單位職稱: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兼任教授 主持人 | 林志興(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前副館長) 與談人 | 陳俊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地點 |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館舍化的部落、部落化的館舍、及不館不舍的部落--臺灣經中國轉北海道到寮國
講座一開始,主講人謝世忠教授首先談到,「部落」一詞許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往往在不經意間就用上,但很少人去深思該怎麼理解「部落」這個詞。從生活於其中的原住民族人到國家政體,對於「部落」都有一番管理、處置的想法,然而在「部落」看似簡單、自然的表象,其實帶著點神秘屬性,這樣的神秘性也似乎不曾有人想去揭穿。事實上,部落就是部落,有部落才有原住民,兩者相互連結,無法切割。在此次講座中,謝教授由兩個關鍵要素切入探討「部落」:一是從部落的館舍樣態著手,以博物館的概念來與部落進行對比,可概分為「部落像博物館」及「博物館像部落」兩種型態;另一則是比較不同國家地區部落的景況,包含日本北海道愛努族、中國雲南西雙版納傣族、寮國北部Tai-Lue人及臺灣原住民族等。 首先,日本北海道愛努族最為國人熟悉,也曾與臺灣原住民族互訪多次。愛努族為適應平地生態的群體,以鮭魚為主要的動物性蛋白質來源,有些住民也獵捕鯨魚,因此聚落多位於河口、海口沿岸。1868年末代江戶幕府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13)還政於日本天皇,展開日本歷史上的「明治時期」,隔年在沒有任何正式協商的情況下,明治政府將愛努族人世居的「蝦夷地」納入日本行政範圍內,易名為「北海道」。隨後頒行的戶口制度在北海道施行,將愛努人納入行政上的「日本人」,迫使學習日語,採用日本姓名與服飾,責令停止刺青、漁獵及祭祀等習俗。此外也強制族人遷移或沒入土地,鼓勵內地人移民北海道從事開拓工作,愛努族人遂逐漸成為「少數民族」。接著,政府又以原有居住屋舍形式不符合消防安全規範為由,禁止居住,自此舊有自然村落(部落)全數瓦解消失。 如今愛努族人四散於北海道各地,各個家戶都被日本移民的家屋圍繞,從外觀上也無從分別差異,族群生活被限縮於自我家居室內,雖然也有些後天人造的展示村落被愛努族人視為顯現族群特色的「神聖空間」,位於北海道道東地區的阿寒湖南岸有一座名為「阿寒湖アイヌコタン」的觀光部落,就是這樣的展示村落。謝教授指出,日本人對「部落」一詞有一種原始傳統的意象想像,而這塊以「部落」為名的區域裡,有雕刻或繪畫出愛努古代樣態的視覺物品,也有強調自古流傳的歌舞表演。觀光客至此除了感受部落氛圍外,也以此來認知愛努作為原住民族的整體模樣。在這個觀光部落裡,雖然有愛努族人,但他們僅是店員,而非真實住戶或土地擁有者。這個「部落」就好像圍著無形圍牆的博物館舍,提供展示、陳列愛努生活的空間,這就是部落館舍化的典型。一旦離開此一無形博物館舍,愛努部落便不復存在。不過,謝教授也觀察到,目前在北海道各地博物館戶外往往有展示用的愛努家屋群,是採用過去部落的樣態構成,愛努族人在沒有自然部落的情況下,卻也發揮了積極的適應力量,透過租借這類建築舉辦傳統活動,賦予文化的真實性,也算是爭回失落的部落。 接著,我們把目光轉向中國雲南西雙版納,歷史上稱為「擺夷」或「白夷」的傣族。1949年國民政府全面撤出中國大陸,卻有部分效忠國民政府的部隊從雲南流亡到泰國、緬甸及寮國交界邊境,持續與共產黨作戰,進而迎娶當地傣族婦女,繁衍後代。歷經數次遷移,部分軍眷落腳中壢龍岡、南投清境農場以及高雄吉洋農場等地,形成極具特色的文化社區。近年來,兩岸的來往也帶進一些西雙版納和傣族的圖文影視資訊。事實上,西雙版納地區曾是中國與東南亞間獨立泰語系小型王國所在地,1950年被中共取消王權,現為「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以傣族為主體,山區另有數個非泰語系的民族。 謝教授指出,傣族傳統生活以「村(bahn)」為基本單位,「bahn」也就是「家」的意思,亦即村內各戶是小範圍的「家」,村子則是大範圍的「家」。每一個村子內有作為信仰中心的專屬佛寺,也由各家協力負責供養出家子弟。各家與地區管理者及中央統治者有一定的義務與權力關係,例如有的負責織布,有的負責鐵製品,有的則擔任守衛工作。然而自王國被取消權力後,各個傣族村落成為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宣傳工具,接近觀光景點的村落被政府徹底改變,轉換成另一種新式建築美感;位於主要幹道旁的村落,則逐一建造具有傣族風味的大型拱門作為門面,以此彰顯傣族文化的「被精緻化」。前者用以招待前來觀看的旅客,後者則給予路過者豪氣、文明的印象,謝教授認為,這兩者就是館舍化和半館舍化的例子。至於在大城市裡,原有的村子在經過城市的發展後,名稱雖在,但原建築與風味都已消失,居民也不知去向,這是不館不舍的現況。另外在勐罕鎮,則是在財團的規劃下,將多個村落圍為「傣族園」,提供遊客觀看,收取門票獲利。居民每日展演傣族文化,例如園區內斗大的標語寫著「天天歡慶潑水節」,由婦女於上午、下午各演出一次潑水節情景,謝教授認為,這是將村子虛存及部落化的館舍型態。 接下來的例子是寮國最北部勐新(Muang Sing,寮文ເມືອງສິງ)地區的Tai-Lue人,Tai-Lue人與寮國主要群體寮人都屬泰語系,也都信奉南傳佛教,不過由於該族位處中國、寮國交界處,在文化上受到中國影響,也敬拜中國北傳佛教的彌勒佛,與一般僅崇拜釋迦摩尼佛的南傳佛教有所差異。Tai-Lue人與前述西雙版納傣族同源,歷史上兩群貴族間有過通婚,同屬中寮邊境的小型泰語系王國。在19世紀後半,法國逐漸滲入中南半島,境內各個小王國陸續臣服,首都位於琅勃拉邦(龍帕邦,寮文ແຂວງຫລວງພະບາງ)的寮王國也成為法國保護國。不過,由於法國於中南半島的統治主力位於越南,對於寮國境內諸小國的管理較為寬鬆。除了必須提供勞力與稅金給新殖民者之外,各地得以維持社會文化的獨立性。隨著20世紀法國殖民勢力退卻,寮王國重新獨立,卻在1975年遭共產黨取代,成立奉行共產主義的寮人民民主共和國。現今寮國頗為依賴中共,卻也接受法、日、韓等國的資金援助建設,本身相當貧弱。 中央的不振也意味著無暇管理地方,因此各地村落的獨立性得以繼續維持。謝教授進一步解釋,所謂的「獨立性」指國家社會乃至居民們幾乎沒有將其館舍化提供展示的必要性,各村原始風貌因此得以大致完整保留,卻也促使歐美背包客絡繹不絕,前來親見所謂「原始傳統」是何面貌。值得說明的是,此處不館不舍的自然村落和西雙版納城市裡的情況截然不同,前者仍精神奕奕地活出自我,而後者卻因國家政治的干預及資本消費的力量,深受衝擊。可以說,西雙版納的自然村落與北海道愛努族都已不復存在,如果想「看見」愛努部落文化或傣族村落文化,就必須到觀光密集處參觀館舍化的樣態。而現代化進展緩慢的Tai-Lue村落,反倒保留了最初的原始面貌。 最後,謝教授回到了臺灣原住民族的情況。在臺灣,主管原住民族的機關單位有固定的部落統計數字,族人同胞提到「部落」一詞也極其自然日常,一般國人只要提及原住民族,「部落」一稱往往脫口而出。然而,所謂的臺灣原住民「部落」究竟意味著怎樣的樣態?「部落」是否就永久歸屬於原住民族所有?謝教授認為,國內翻譯「部落」一詞的英文時,總不假思索地使用「tribe」這個字,但這個字其實充滿負面意涵,基本上是為了否定原民群體為「國/民族實體」(nation)而創立的弱人團體代稱。再觀察原民部落的樣貌,首先是在山地平地化的三十年間(1950-1980),建屋取材從傳統自然木、竹、石轉為水泥,80至90年代間則是水泥房化部落和殘餘傳統屋舍並存的樣貌,而90年代興起的社區總體營造觀念,不僅影響了臺灣農村,也打造了近三十餘年原民部落的面貌。 在原住民地區,社區營造的目的在於使部落「更像個部落」,但就謝教授的觀察,部落其實是逐漸館舍化,縱使部分部落沒有明確的大型營造計畫,各別團體家戶乃至個人也都在進行小型的社區營造,然而也因為缺乏整體性的規劃與呈現,容易形成內在的矛盾,或隨著時間,疏於管理及維護,反而加深其不協調感。不過,仍有忽略或被忽略於社區營造風潮下的部落,反而比較像寮國不館不舍的部落。總體而言,臺灣原民部落是持續往館舍化的路徑前進,從傳統到社區營造的70年間,要使失去傳統的部落返回傳統,大多是通過視覺上的認證,亦即藉由外在裝飾物(如繪畫、雕刻等)的添加,來證成部落文化的存在,卻也多呈現散置各點的現象。 謝教授最後總結,藉由臺灣、日本、中國及寮國等四地的比較,我們可以發覺部落或自然村在當代的情境下,大多受到國家的干預與擺佈,例如中國與日本即是如此。現代國家只要經濟條件允許,必然深入介入部落或自然村,然稍有不慎,可能將使其整體性受到破壞,如臺灣原住民部落便常見水泥化和剩餘傳統建築並存的雜亂現象。在寮國,部落得以常保傳統的基礎是建立在國家貧弱不足以干擾的前提下,卻也反而成為背包客趨之若鶩的原始樂土,與日本、中國的大眾觀光截然不同。不過,若說部落想維持傳統樣貌必須仰賴國家的不干預,似乎有些不切實際,畢竟族人都生活於現代世界,所有現代社會的產物終將進入部落,在無形中默默改變部落。正由於部落或自然村存在於當代,終究無法避免矛盾的複雜屬性,畢竟現代性與傳統多所抵觸。然而對於原住民而言,部落不僅是族人聯繫歷史與未來的節點,也是生命繁衍的場所,更是族人或本地人的最後淨土(territory)。不過,國家的介入將使部落的軟實力產生質變,部落就容易轉化成館舍化,有如參觀博物館。另一型態則是資本以部落樣態呈現擬博物館,也就是部落化的館舍,讓旅人身歷其境,以感官留下印象。而部落居民雖得以藉由展演生活營生,是否也意味著財團將掌握村落的面貌?最後,臺灣的社區營造固然用意頗佳,但隨著各自所需不同,經濟條件和生活營生條件的差異,以致於造成新舊不均,這也是值得部落居民深思的議題。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3卷3期,頁88-93。 |
||
|
|
指導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協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聯絡電話:(05) 310-6273 電子郵件:mostsalon@gmail.com 地 址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