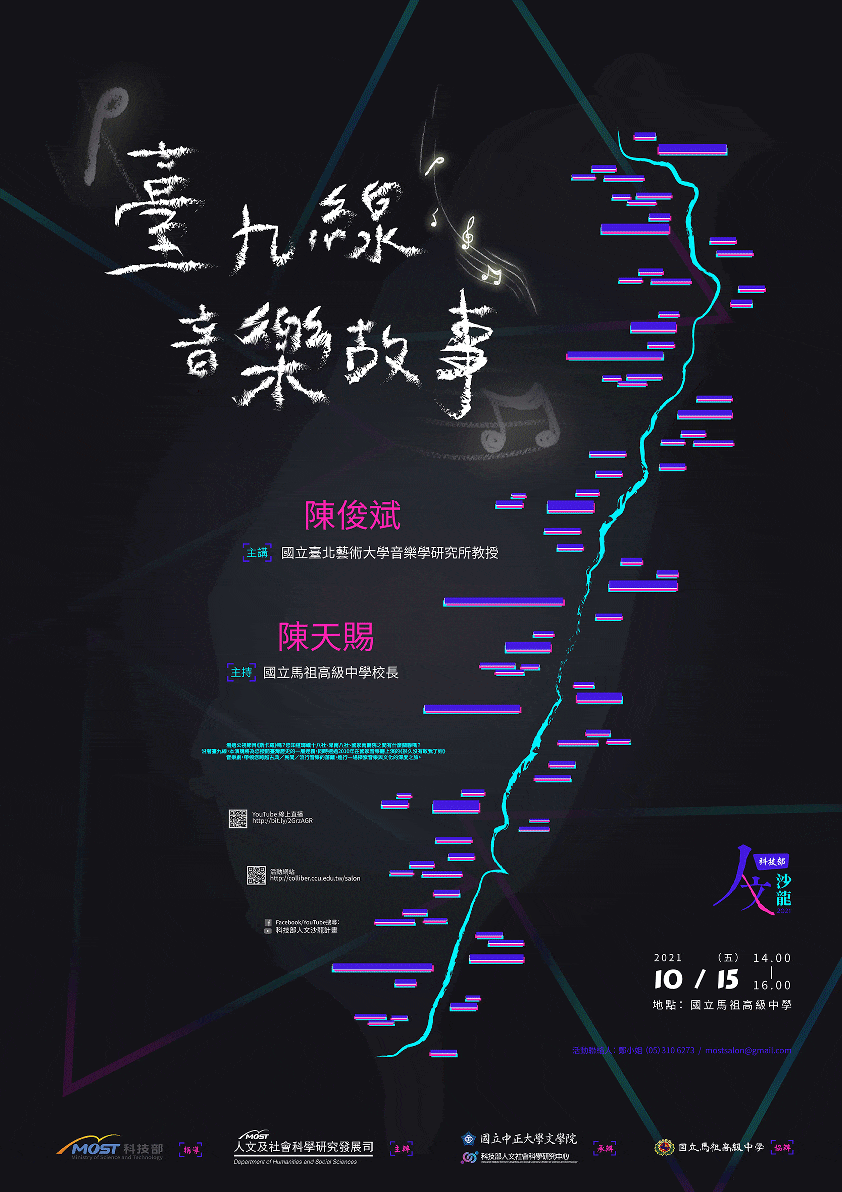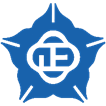|
第49場 |
||
|
日期:2021-10-15 講者姓名:陳俊斌 單位職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 | 陳天賜(國立馬祖高級中學校長) 地點 |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臺九線音樂故事
講座初始,主講人陳俊斌教授以公視劇集《斯卡羅》引言,此劇以陳耀昌醫師之歷史小說《傀儡花》改編,開拍及宣傳時亦沿用書名,然因過程中意識到「傀儡」是往昔對原住民族的蔑稱,後經由網路徵件、票選後定名為《斯卡羅》。故事描述1867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又譯羅發號)於恆春外海意外觸礁,船員登陸求生,誤入原住民斯卡羅領地,被視為侵略者,發生武力衝突,導致船長夫婦及船員等十三人罹難。事後美國派遣軍艦、水兵遠征討伐,登陸後反遭擊敗,帶隊官麥肯齊(Alexander
Slidell MacKenzie, 1842-1867)少校陣亡。美方再令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1830-1899,法裔美國人,另有中文名李讓禮、李善得)循外交途徑處理此事。李仙得因不滿清廷駐臺官員態度消極推諉,於是親至斯卡羅領地與大股頭卓杞篤(Cuqicuq
Garuljigulj, ?-1872)談判,雙方達成協議,訂定日後海事受難者的求援原則,並於1868年2月底完成書面協定,即為「南岬之盟」。陳教授解釋,所謂的「斯卡羅」即是由臺東知本舊部落遷移至恆春半島的卑南族人,憑藉武力與巫術獲在地排灣族認同,於今日滿州、永靖、網紗與龍鑾潭地區建立部落。值得說明的是,斯卡羅往往被稱為「排灣化的卑南族人」,然而當時原住民並不存在「族」的概念,而是使用「人」或「人群」的概念,今日我們習稱「某某族」的用法,其實是由於日治時期學者分類與便於治理等因素而產生。 羅妹號事件後,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中也可見斯卡羅人的身影,征臺日軍指揮官西鄉從道(1843-1902)甚至與斯卡羅領袖合影。牡丹社事件也改變清廷治理臺灣的態度,轉為積極經營,增設府縣,並對東部及原住民地區「開山撫番」。卓杞篤之養子、後繼任大頭目的文杰(Bungekaic
Garuljigulj, 1854-1905)也因協助清廷於恆春築城及調停各部落有功,前後被賜漢姓「潘」及五品軍功。1895年臺灣割讓日本後,潘文杰也發揮影響力,調解族群紛爭,協助日軍平定後山,深得臺灣總督府倚重,因而獲頒勳六等瑞寶章(日本勳章,授與在公共事務有功者),並委任為恆春廳參事。陳教授認為臺灣近代歷史發展脈絡中,這群來自臺東卑南族的斯卡羅人發揮的影響與作用不容小覷,他們的發源地臺東的卑南族人又是什麼情況呢?若我們仔細端詳現今卑南族部落的分布情況,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幾乎都鄰近臺9線公路。是什麼因素造成這種現象?臺9線與卑南族人有什麼關係?這條綿長的公路又為他們帶來了什麼? 1978年後臺9線曾是全臺公路系統里程最長的公路,又稱東部幹線,是連結臺灣東部最重要的縱貫幹道。經歷蘇花改、南迴改等截彎取直工程後,目前全長為454餘公里,為現今臺灣公路系統第二長的路線,僅次於臺1線。臺9線起點位於行政院、監察院的路口處,沿途經過立法院、教育部、臺大醫院、中正紀念堂、臺灣大學等臺北政治、文教樞紐地帶,往蘭陽平原延伸,穿越花東縱谷,並於南迴公路段越過中央山脈尾端進入屏東縣枋山鄉楓港,連結西部幹道臺1線,兩者所形成的環島系統,可說是構成臺灣交通運輸的兩大動脈。花、東兩地的臺9線路段,大致是1930年代日本統治時陸續興建,其中也包含利用清代舊道基礎拓寬改造者。同時,日本政府也將原先雄霸臺東平原的卑南族各部落由舊址遷移至公路附近,如今所謂「八社十部落」如知本、利嘉、泰安、初鹿、南王(普悠瑪)、寶桑等等,幾乎都鄰近臺9線,這反映了日本政府基於行政與管理上的方便,透過現代化建設將原住民納入國家統治的意圖。對部落而言,這條幹道也成為卑南族人聯絡內外的窗口,部落相關歲時節慶活動亦泰半於臺9線公路兩側舉辦,成為部落居民日常經驗與生命記憶的一部分。 由臺9線起點沿著中山南路步行約20分鐘,便可看到「中正紀念堂」內矗立著兩座醒目的中國宮廷式建築,分別為國家音樂廳及戲劇廳,並稱為「國家兩廳院」。作為國家文化表演的藝術殿堂,兩廳院可說具有崇高地位。2010年兩廳院「旗艦計畫」、也是第二屆臺灣國際藝術節(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簡稱TIFA)主打節目之一的《很久沒有敬我了你》(以下簡稱《很久》),是以臺灣原住民為主題的音樂舞臺劇,擔任總策劃的角頭音樂創辦人張四十三(本名張譯平)則稱它是一部「電影.音樂.劇」。此劇由胡德夫、陳建年、紀曉君、紀家盈(藝名家家)、吳昊恩及「南王姊妹花」(李諭芹、陳惠琴、徐美花)等卑南部落族人擔任主要演唱者,並由簡文彬指揮國家交響樂團演奏。故事講述一位國家交響樂團音樂總監為了逃避工作壓力,來到臺東卑南族南王部落,身為漢人的他,卻因為當地族人的歌聲喚起兒時回憶,感動之餘,他提議將這些歌聲與管弦樂結合,帶往國家音樂廳演出。這個提案起初遭到族人拒絕與質疑,但在男主角參與部落大獵祭(mangayaw)後,獲族人接納與肯定,故事最後在族人於國家音樂廳光榮登場中結束。 當年音樂劇演出後又於「自由廣場」上舉行大會舞,由南王部落族人帶領觀眾跳舞,陳教授的岳父也曾是其中一員。事實上,不僅陳教授的岳父來自南王部落把高揚(Pakawyan)家族,劇中大部分表演者也都是熟悉的南王部落族人,對於陳教授而言,欣賞這部音樂劇的動機,並非受劇情內容或劇中某些特定樂曲吸引,而是因為人際關係的牽引。這讓身為音樂研究者的他注意到,大部分臺灣學者關於音樂表演的論述,幾乎都以樂曲作為分析的文本,鮮少關注表演者間及表演者與觀眾的關係,亦即學術論著所強調音樂本身的意義,以及實際音樂行為所產生的意義,兩者存在著若干差異。這種現象引發了他對於研究者立足點與研究取徑的思考,以及對原住民音樂現代性及當代情境的探討,也涉及音樂、人及空間等更宏觀層面的研究。陳教授直言,《很久》雖以戲劇形式表現,但吸引一般觀眾的地方可能並非是劇情,而是音樂與演唱者。這些主要歌者都曾經出過專輯,更曾在全國性音樂獎項(如金曲獎)中獲獎,其他搭配的歌者也都是其親屬,演出曲目或樂曲與南王部落關係亦為密切,可說是以歌曲連結南王部落的音樂故事。 在《很久》節目手冊中被列為主要歌者之首的胡德夫,是唯一不屬於南王部落的成員,陳教授認為這是為彰顯他作為「臺灣民歌之父」的地位。具有卑南和排灣族血統的胡德夫,在劇中出現的時間並不長,但由其擔當領唱的設計,可凸顯長者地位與世代傳承的意味。另外,原為警察的陳建年在喜愛原住民音樂的聽眾間頗具知名度,也曾得過多項大獎,尤其2000年從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奪得「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獎」及「最佳作曲人獎」,殊為不易。此外,他的外公即是被尊為「卑南族音樂靈魂」的陸寶森(1910-1988,原名Baliwakes,日治時期因皇民化運動改名為「森寶一郎」,後再改為漢名),其自1940年代起,陸續寫作約三十首卑南母語創作或譯作歌曲,帶動卑南族文化復振運動,對於陳建年的影響亦為深遠。稱陳建年為表舅的紀曉君,曾於2000年獲金曲獎「最佳新人獎」,妹妹紀家盈也是知名歌手,與表舅吳昊恩組成團體「昊恩家家」,於2007年獲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獎」,後逐漸踏足主流音樂市場。「南王姊妹花」彼此有親戚關係,成員各自有自己的工作,是因唱歌才組成團體。她們錄製的兩張專輯中,第一張同名專輯於2009年獲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及「最佳演唱組合獎」。因此,由該劇主要演唱者陣容來看,其演唱實力與魅力備受肯定。陳教授於研究過程中訪談此劇總策劃張四十三時得知,其實籌備、設計的過程相當曲折辛苦,對於演出後迴響頗佳亦感到意外,他認為除了歸功於幸運找到適合的團隊夥伴外,這些原住民表演者也讓這部劇增色不少。 此劇分為二十幕,基本上每一幕包含一首主要歌曲或樂曲,內容與劇情也不必然相關。這些核心歌曲連結了南王部落卑南族人的音樂經驗,大致可指涉四個年代:傳統年代、唱歌年代、現代民歌與原住民運動年代、金曲年代。「傳統年代」的音樂包括卑南族傳統音樂及原住民共通的音樂;「唱歌年代」指陸森寶於1930-1980年代間受日本「唱歌」(しょか)教育,並將其與部落傳統音樂元素融合,於戰後仍持續創作具有「唱歌」風格的族語歌曲的年代;1970-1990年間原住民社會運動及現代民歌活動興起,代表人物即胡德夫;金曲年代則是指2000年後南王部落歌手多次榮獲金曲獎獎項,以陳建年、吳昊恩等人為代表。陳教授認為這些歌曲或樂曲的安排,體現了南王部落當代音樂發展的脈絡,曲目的連結呈現了一段從「唱歌年代」到「金曲年代」的歷史,其中尤為凸顯了陸森寶在南王當代音樂發展中的關鍵地位。劇中演唱了陸森寶〈美麗的稻穗〉、〈卑南王〉兩首歌曲,以及一首由其創作〈懷念年祭〉所改編的演奏曲,其曲目數量為全劇之冠。 〈美麗的稻穗〉是陸森寶於1950年代為在金門參戰的卑南子弟所寫,出現在劇中第六幕與最後一幕。這首歌共有三段,但劇中僅將第一段演唱三次,陳教授認為如此安排似乎暗示歌詞內容並非演出重點,而是藉由相同旋律在不同演唱形式的組合,呈現多層次的變化。由紀曉君領唱的〈卑南王〉出現於第十六幕,乃是陸寶森改編自佛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 1826-1864)的〈老黑爵〉(Old Black Joe,又譯作老黑喬、老黑奴),歌詠教導卑南族人農耕的祖先Pinadray。〈卑南王〉呈現許多「唱歌」作品的特色,應該是陸氏較早期的作品。「唱歌」為日本政府於十九世紀末由西方引進的音樂教育其中的一個元素,乃利用西方現成歌曲旋律另外重新填詞,此方式隨著日本殖民也成為臺灣音樂教育的一部分。這個殖民遺緒奠定西方音樂在臺灣的發展基礎,也成為原住民音樂發展的養分之一。〈懷念年祭〉是陸森寶於1988年以大獵祭為主題所創作的歌曲,然而僅完成一段歌詞便已辭世。歌詞中他以外地工作的族人口吻,述說自己雖無法常回到部落,但不會忘卻傳統。在《很久》中此曲出現在第十四、十五幕,但改為交響樂團演奏的版本,搭配南王大獵祭紀錄影片的方式呈現,影片中並未出現大獵祭現場的「劇情內聲音」(diegetic
sound),而是由音樂廳現場的管弦樂演奏為「非劇情聲音」(non-diegetic
sound)。 大獵祭是卑南族最為重要的祭儀之一,包含猴祭(少年年祭)、除喪等環節,源自古代之狩獵祭儀、團體軍事訓練及部落報復行動。傳統卑南社會中,男性的成長主要分為兩階段,未成年時需居住於少年會所接受訓練,成年後則進入男子會所,成為部落戰力,因此在大獵祭正式舉行前的猴祭,是以少年為對象的縮小版大獵祭,目的在於訓練少年膽識、狩獵技巧、團隊服從性,作為進入成年階段的準備。其後的大獵祭,則在出發前往營地行獵訓練後,部落婦女會以竹子搭建「迎獵門」迎接凱旋歸來的眾男子,為其更換禮服,並舉行除喪祭儀,接著開始歡唱宴飲。除喪由巫師主持,驅逐哀怨與晦氣,迎向新的階段(翌日亦即是「新年」),前一年居喪的人們也因此解除相關禁忌。陳教授認為,《很久》以大獵祭活動影片及〈懷念年祭〉的搭配,相當具體且真實地呈現南王部落大獵祭的過程,以跳接與剪黏的方式呈現於舞臺上。臺9線上的音樂故事提供了理解音樂表演與文化意義的一些線索,作為故事主角的卑南族人,歌唱是他們溝通與表達情緒的途徑,也是聯繫家庭情感與部落成員的重要場域。當他們登上現代劇場的舞臺,這樣的感染能力仍可觸動觀眾,於是音樂成為不同人群對話的時空,允許表演者與聽者在其中來去自如,而音樂學者正是這個時空的領航者。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3卷1期,頁124-129。 |
||
|
|
指導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協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聯絡電話:(05) 310-6273 電子郵件:mostsalon@gmail.com 地 址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