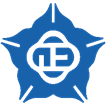|
第46場 |
||
|
日期:2021-04-29 講者姓名:李卓穎 單位職稱: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 | 李道緝(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與談人 | 陳元朋(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潘宗億(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大眾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地點 | 國立東華大學人社一館第二講堂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互文性的書寫行動: 從明代蘇州的記憶爭辯談起
新朝為前朝撰寫歷史,是中國傳統「改朝換代」的慣例,其書寫內容也意味著勝國一方的立場與角度。但為前朝寫史並非官方特權,具備書寫能力的士人可能因不同因素投身此一工作,特別是經歷政權更迭過程、與前朝關係密切地區之遺民士人,書寫內容與詮釋角度可能與官方範式有協作或衝突的不同立場。主講人李卓穎教授以蘇州為例,說明當地於元明易代之際的十餘年間,經歷了元朝、張士誠(1321-1367)、朱元璋(1328-1398,即明太祖)等不同的實質統治者,亦即「元明易代」並非由元朝直接轉換為明朝,而是經歷過非元非明的張士誠統治階段,因此蘇州人民如何看待及理解張士誠,必然與元、明統治有著連動關係,有關朝代更迭中的書寫,也反映了遺民士人的認同傾向及身分政治。 朱元璋陸續擊敗陳友諒(1316-1363)、方國珍(1319-1374)及張士誠後,統一中國南方,於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1368)於應天府即位稱帝(原為元之集慶路,即今之南京),因此歷史上以此作為明朝起始年。該年朱元璋趁元朝內訌乘機北伐,攻克元大都(今之北京),元惠宗(妥懽貼睦爾,1320-1370)退至上都(為避暑行宮,於今內蒙古境內),仍保留「大元」國號,史稱為「北元」。然而當時關中仍有元將擴廓貼木兒(約1315-1375,漢名王保保)持續與明軍對抗,乃至洪武五年(1372,北元宣光二年)時曾於漠北擊潰明軍,阻斷朱元璋占領元朝全部故地的企圖。北元勢力一直延續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即北元天元十年),北元後主脫古思帖木兒敗於藍玉(?-1393)所率領的十五萬北伐明軍,倉皇逃奔,不久遭到殺害,自此蒙古不再使用帝號、年號。李教授指出,據此可知「易代」是個因時序而有異的過程,如以朱元璋攻克集慶並改為應天府的1356年起算,或許得到擊敗北元後主的1388年才算完成。這個長達三十年左右的過程,期間朱元璋不斷調整策略,可見歷史的走向尚有諸多不確定性,並非直線進行。 若「易代」是個可從慣常以為的時間點順著時序向前、向後延展,且具有不確定性的過程,那麼也是個因地域而有差異的現象。更具體地說,不同地域因納入明朝統轄範圍的時間不同,可能被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也可能因各個地域不同的特性,而與新朝形成不同的關係,故對於不同地域的「易代」經驗可能無法以一概全,仍須著眼於地域因素所形成的差異,那麼「易代」的歷史性(historicity)就可以從時間和空間上,成為立體而可考察的對象。以此作為框架,也可依著時間和空間的向度,處理人們「易代」經驗的複雜性和特殊性,換言之,「如何易代」也成為可分析研究的課題。李教授進一步說明,前述的思考著重的是「易代」本身,所涉及的是具有直接易代經驗的人物,可稱之為「易代事件」的第一代,然而「易代事件」並非僅對於第一代人物有直接作用,而是也影響後代如何書寫、看待、反應、理解「易代事件」之意義。要分析為何書寫「易代」,可由幾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出發,亦即:誰寫(who)?寫給誰看(to whom)?什麼時候寫(when)?如何寫(how)? 基於上述思考,李教授以蘇州為中心進行關於元明易代書寫的思考及研究。從空間上來說,蘇州曾是元末張士誠的主要根據地;由時序上來看,張士誠在蘇州立足了十一年(1356-1367)之久,因此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蘇州地方人士經歷了「元朝→張士誠→朱元璋」的實質統治,故當地士人書寫元明易代的歷史過程,必然涉及對於三者的評價。需說明的是,蘇州士人固然有一手經驗及口耳相傳的歷史記憶,但他們的書寫並非在無限制條件下進行,亦即不可能不受到官方史籍書寫範式的影響與拘束,可說官方書寫範式就是他們必須要面對的對象(to
whom)。明代官方對於元明易代的書寫,最初以《元史》為基本範式,張士誠的事蹟也在朱元璋指派宋濂(1310-1381)、王禕(1322-1373)編纂下寫入此書。該書編成於洪武三年(1370),距離張氏兵敗僅三年左右(when),不過並未為其立專傳,相關紀錄散見各處。《元史》編纂者的立場將元朝視為具有正當性的朝代,對它有極高的讚許,因此敘述張士誠起兵時稱其「為亂」,其餘群雄也被視為是叛亂者,僅有朱元璋是弭平動亂、恢復秩序的「真主」(how)。 另一官方範式為明憲宗成化十二年(1476)編定的《續資治通鑑綱目》(以下簡稱《續綱目》),採用了跟《元史》極為不同的態度。此書認為元朝是個棄禮法、世運否、有待撥亂反正的胡主時代,直斥其為夷狄、外族。在此論述脈絡中,元末群雄不是叛亂者,反而是義軍領袖,如張士誠不再稱為「作亂」,而是「兵起」,同時他在高郵是「自稱」而非「僭稱」為王,可說是脫去《元史》賦予的汙名。不過,既然群雄並非叛亂者,又該如何證成朱元璋的正當性?《續綱目》在朱元璋起兵的「綱」之下錄有耆儒陶安(1310-1368)的獻言,其云:「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這些文字將朱元璋與群雄做了比較,朱之所以突出在於「神武」而不嗜殺,心念非在「子女玉帛」,而在「安天下、救生民」,換言之,朱元璋的起兵是順天應人、弔民伐罪的王者行動,天下歸服也是理所當然的結果。《續綱目》與《元史》範式的不同,其原因之一可能是明朝在土木堡之變(1449)後,有意修改史籍中與北方異族關係的紀錄。這兩種官方範式經過頒布與士人各自取法進行續作後,都有相當的流通,但此一情況在張士誠最重要的根據地蘇州,對士人及一般人理解或書寫這段歷史又有何影響、作用或反動? 洪武初年蘇州府常熟縣曾有一座感念張士誠「浚浦有功」的張太尉廟,雖不知該廟何時廢毀,但至少能說明當地居民在明代初期仍有感懷之心,地方層級也尚有表達這種心意的空間。這樣的情況可能因為日後發生的事件而遭受限縮,這點可由明初蘇州知府盧熊(1331-1380)編纂明朝第一部《蘇州府志》中看出端倪。是書刊行於洪武十二年(1379),並有當朝重臣宋濂的序文,盧熊於書中記錄朱元璋部隊攻下蘇州時「大軍進城,禁剽掠,居民安堵如故」;然而盧熊在自己的詩作〈將還吳述懷兼簡李孟言賢良〉及〈憶先塋〉詩序中卻有大相逕庭的描述。盧熊於詩中言及因奉養病母,無法在城破之時逃去,於是遭逢「亂兵槌戶來,⋯⋯兵怒無金貲,頭顏遭刃劈」的危難;在詩序中更直指「蘇城之西,岡阜相屬,大軍圍攻,自冬徂秋,冢墓多被發掘」。盧氏世居崑山,親身經歷蘇州城陷、張士誠敗亡的過程,對於朱元璋軍隊的行為當是耳目親見,然而這些訊息卻在他寫作《蘇州府志》時全數隱去。事實上,盧熊曾以博士身分執掌蘇州轄下吳縣教育,也曾為張士誠女婿所立之碑篆刻,可見與張士誠政權的關係非淺,之所以請求宋濂為《蘇州府志》作序,李教授推想可能是希望藉由宋濂的名望為此書擔保,同時也透過總編纂《元史》的宋濂確認內容有無牴觸當朝忌諱,因此本書可說是對朝廷謹慎小心的表獻之作,有著壓抑記憶以迎合明朝期待的傾向。 李教授續談蘇州士人陸容(1436-1494)的記錄。其於弘治年間編成筆記《菽園雜記》,該書有兩條與張士誠有關的地方傳言紀錄,第一條稱朱元璋微服出行,詢問一位蘇人老嫗:「『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此條紀錄中蘇州百姓得以全其性命,並非朱元璋的「神武不殺」,而是由於張士誠放棄軍事對抗以保全蘇州百姓的仁德之舉。另一條紀錄則稱蘇州由於曾是張士誠根據地,遭受朝廷重稅報復,成為當地百姓「積久之患」。李教授指出,針對蘇人重稅即使並非朝廷刻意報復,但也與昔日朱元璋傳諭蘇州的招降榜文「永保鄉里,以全家室」的承諾相悖,至少可說是對於歸順者的處置失當。儘管陸容並非元明易代事件的第一代人物,但仍以筆記體記錄蘇州流傳的看法,其所記錄內容也與流通的《續綱目》有爭辯的意味。 另一位蘇州士人吳寬(1435-1504)因於成化年間(1465-1487)任翰林院修撰、弘治年間(1488-1505)預修《憲宗實錄》的機會,得以閱覽宮中禁止外傳的珍貴文獻,亦藉此從《太祖實錄》中抄錄了元明易代過程中關於蘇州的記載,日後輯成《平吳錄》一書。其遵從了《續綱目》的範式,但有許多細節未見於前書之中,其中至正二十五年(1365)以降的篇幅約占全書十分之七,對於朱元璋如何逐一攻略張士誠據地,乃至雙方折衝對抗的細節,都較《續綱目》細緻詳盡,大抵而言呈現真正有仁心的是朱元璋而非張士誠,刻劃朱元璋的王者風範。吳寬在書中兩處特意標明朱元璋部隊秋毫無犯,一處強調平定蘇州過程中「居民晏然」,實與前述陸容所記內容頗為逕庭,事實上兩人世代與生活世界頗為相近,吳寬對於當代口傳說法亦應有所聽聞,卻對其顯然保持了距離。李教授強調,這不是說吳寬撰輯該書之目的在於駁斥口傳說法,事實上他仍在幾處微妙但重要的敘事中,透過刪減、擷取文獻資料的方式,隱含了個人對於元明易代過程中張士誠、蘇州及對朱元璋的意見。具體來說,他更傾向將張氏的失敗歸結於治理的失誤,也肯定其於亂世中提供徬徨人們庇護保全之地,以及張氏對待士人的寬厚態度。 吳寬的《平吳錄》大概在弘治後期─即十五、十六世紀之際─於蘇州流通,引起蘇州士人的注目與反應,大致落實於兩種書寫型態,其一是王鏊(1450-1524)編撰的《姑蘇志》,另一為再引蘇州地方傳言入筆記,與吳寬針鋒相對的書寫行動。於《姑蘇志》中,王鏊遵循了《續綱目》的範式,對於評價張士誠所持態度也較吳寬嚴峻,全無一絲肯定之詞,雖不認為張士誠是叛亂者,但仍貶斥其乃非為蒼生福祉而又殘暴的統治者,可視為是此前官方範式流通後,又一產生具有官方色彩的理解。吳寬與王鏊都是頗負盛名的蘇州士人,一致採用了抑遏地方傳言且重述《續綱目》的書寫行動,也引起其他蘇州士人以地方傳聞撰寫筆記作品的反制,其中以黃暐(1466-?)《蓬窗類紀》、祝允明(1461-1527)《野記》及楊循吉(1458-1546)《吳中故語》為代表。在他們的紀錄中,張士誠以己身解救蘇州百姓的決心,與朱元璋部將常遇春(1330-1369)或湯和(1326-1395)屠殺蘇州城民的作為形成強烈對比。李教授指出,這些蘇州士人訴諸鄉野傳言撰成有異於官方的另一套理解,其書寫目的不在紀實,而是刻意抗拒《續綱目》範式的行動,他們承認張士誠缺乏天命眷顧,但不認同官方範式將其描寫得一無是處,也藉由凸顯張士誠的某些側面,表達他們對元明易代的理解及關切。 李教授總結,不論經歷元末張士誠統治的第一代,或其後第二、三代的蘇州士人,其在撰寫易代事件時,都是以「互文性」脈絡進行書寫行動,因此研究易代書寫必須深入各別著作所使用的概念、敘述架構及遣詞用句,也必須兼顧其與相關文本的互文性分析。其目的不僅是彰顯個別文獻的獨特性,更重要的是從論述爭辯性的角度理解個別著作的獨特性,都是經歷選擇而採取不同書寫行動的產物。他們的著作不論是理性論述、倫理訴求乃至情感張力的展示,都界定著其與過往、現今政權的關係,並成為後來書寫者重新界定自身與易代事件及當前政權關係時,必須在情感、倫理、論述上或揚或棄的對象,進而形成如何才是合宜統治的認定,以及對未來的期待。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2卷4期,頁118-124。 |
||
|
|
指導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協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聯絡電話:(05) 310-6273 電子郵件:mostsalon@gmail.com 地 址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