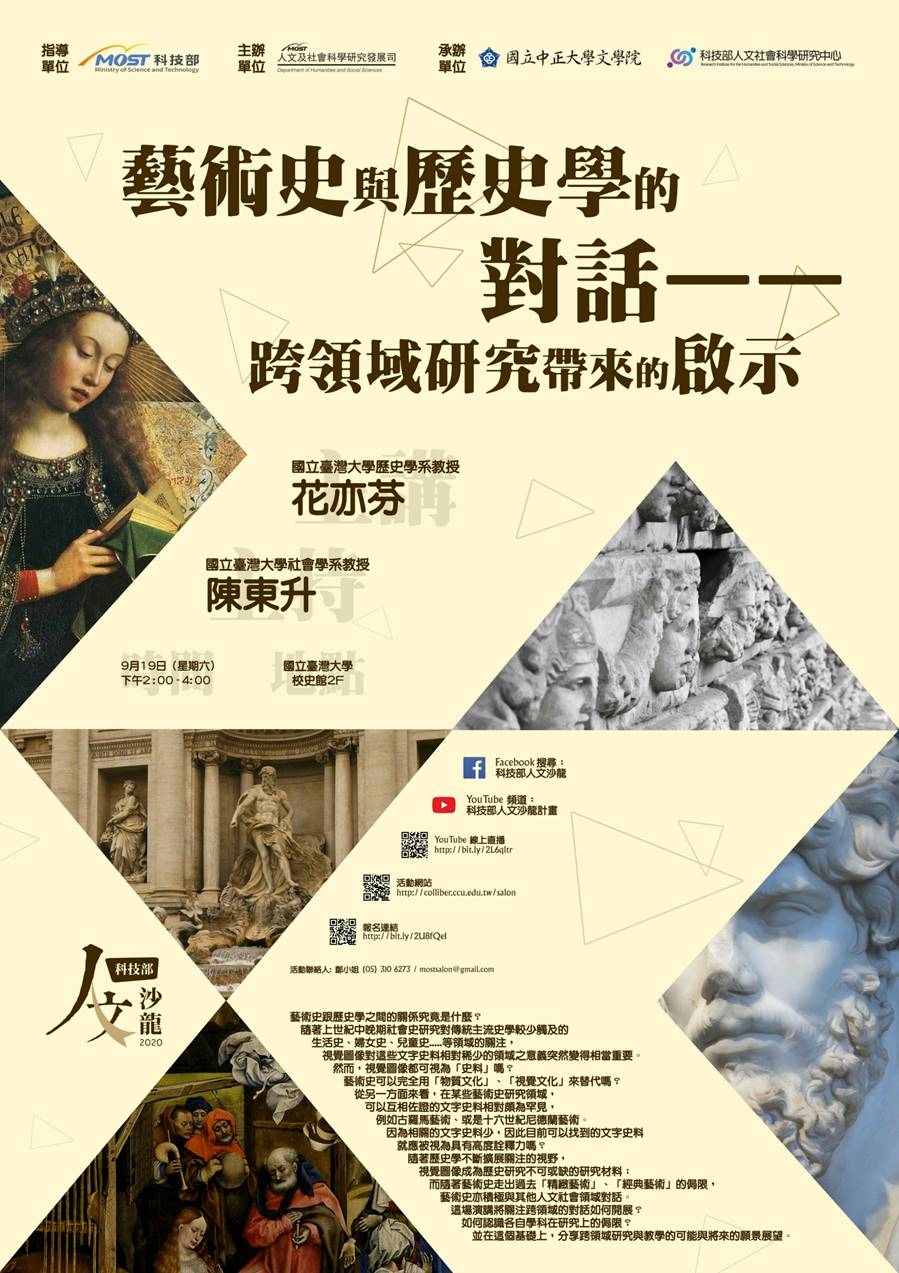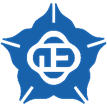|
第38場 |
||
|
日期:2020-09-19 講者姓名:花亦芬 單位職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主持/與談人 | 陳東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地點 | 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2F(中央展區)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藝術史與歷史學的對話--跨領域研究帶來的啟示
不論個人有限的生命,或由人類發展的長遠歷史來看,「知識」是藉由不斷地累積、改變而成,大學中所謂「人文社會學」的知識體系亦復如是。在本次人文沙龍講座,花亦芬教授談到人文主義(Humanism)是自文藝復興時代從中古artes liberales(原句為拉丁文,一般譯為「博雅教育」)獨立出來。中古時代的大學將知識基本分類為七種領域:文法、修辭、辯證、天文、幾何、算數、樂理等,前三者稱為「三學」(Trivium),後四者稱為「四術」(Quadrivium),是中世紀大學的主要科目。由此七種領域來看,當時所謂的「人文學」實為人文與自然知識的綜合。至19世紀時,歐洲各大學形成各自的專業「科系」,並逐漸構築其「方法論」,「方法論」可說是各科系作為獨立存在的支撐,尤為強調專業性。進入日趨複雜化的現代世界,專業知識生產的細碎化,使學科知識專業化反而面臨諸多困境,故跨領域研究的必要性與迫切性逐漸增長,因此21世紀可說是強調跨領域對話整合的世代。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透過歷史知識的門徑,走入藝術創作的世界?藝術史跟史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視覺圖像就是視覺史料嗎?對視覺作品的解析一定得依靠白紙黑字的證據嗎?這些是歷史學與藝術史在進行跨領域對談時經常會遇到的問題,亦是花教授長年研究的重要課題。 花教授認為,圖像可視為是一種視覺的溝通,是為達到某一社會溝通目的而形成。歷史學者開始運用圖像資料,乃是源自歷史學研究領域的擴大。過去史學研究極為仰賴官方文獻、史料,或說是由主流價值所篩選、呈現、保存的訊息,今日的研究者開始關注過去被邊緣化、或被主流價值刻意忽略的人群或者是個人,但正因為過去這些弱勢族群缺乏足夠的文字史料記載,因此視覺圖像成為新的選項,可供歷史研究之用。視覺圖像除了提供訊息,補足史料外,也是一種史料多元化的表現方式。然而,視覺圖像的解讀,絕非「看圖說故事」般簡單、直接,花教授強調,不論使用藝術品、攝影作品等視覺圖像都要很小心,因為圖像所呈現的未必是真實世界的映射。以荷蘭畫家Pieter
de Hooch(1629-1684)的畫作A Woman Preparing Bread and Butter for a Boy為例,畫面中屋內的一位母親正為麵包塗上奶油,她身旁站著的孩子正低著頭為食物而禱告,透過敞開的前門,可以看見在陽光散落處的學校,可知她的孩子正準備啟程前往上學,門上的小閣樓裡擺著幾本書與燭臺,或許象徵著知識與光明,亦即教育帶給下一代的啟發。花教授指出,荷蘭於1648年自西班牙獨立建國,成為歐洲近代第一個共和國,Pieter de Hooch此畫約作於1660年,亦即荷蘭建國之初,當時的藝術表現特徵是風俗畫的大量出現,風俗畫是描寫各種日常生活的情景,但該畫能否作為當時荷蘭人日常生活的觀視(Reality)?花教授認為,以前的研究常將繪畫資料視為是視覺的史料,用以佐證當時人們的生活情景,但圖像資料其實未必如照相般真實反映現實世界,由Pieter
de Hooch此畫所描繪的上學場景、家中呈現的書香氣氛,其實是畫家,或當時社會對於新起造國家中產階級對教育文化理想(Ideal)的投射。 花教授認為,視覺圖像並不是表現(Represent),而是反映(Reflect),因此,歷史研究使用圖像時應注意圖像關聯到的脈絡,以及圖像語言、圖像隱喻與圖像內在的對話傳統。圖像作為溝通系統,實際上有其所使用的「語言」模式,相關主題的畫作也有其內在的傳統,致使畫家依循相同模式進行繪製。如英國攝影家John
Thomson(1837-1921)曾於1871年來到臺灣,拍攝了四十餘張相片,包含當時臺灣平埔族的生活樣貌。相片中平埔族人或站或坐,或以不同的角度、姿態於鏡頭前,彷彿是現代偶像團體的宣傳照。然而這樣的拍攝現象,並不意味當時平埔族人因個人意識而擺出這些姿勢,或因風俗習慣而做出這些反應;事實上,John
Thomson所拍攝相片的販售對象,不乏英國人類學、民族學等相關學會,正因這些照片可作為人種學研究資料,因此需盡可能拍攝不同的角度與樣貌,也就是說,這些平埔族被攝者所呈現的不同姿態,實屬拍攝者刻意為之的結果。另一例證是以色列古老的五餅二魚教堂(Church
of the Multiplication),該堂中有一塊發掘出來的石灰石,被信眾認為即是《聖經》故事中耶穌放置五餅二魚處,因此於其上設置祭臺,臺前則有馬賽克鑲嵌畫,描繪了兩條魚和一籃餅,但細看畫中餅數僅有四塊。花教授指出,這並不是圖像的失誤,或者僅是作為裝飾使用而不加深究的插圖,事實上該圖像的使用乃為配合聖餐禮儀式,主祭者手中另有一塊真實的大麥餅,在儀式中會分給與會者,也就是說,該圖像的作用是為重現儀式的「現場」。因此瞭解圖像背後的脈絡意涵,是歷史研究者應注意的面向,不能僅由表象便直接下斷言。 關於圖像內在的對話傳統,花教授以法國畫家Hyacinthe
Rigaud(1659-1743)為路易十四繪製的加冕畫像作為例證。在畫中,皇冠並非戴在路易十四頭上,而是在一旁檯上陳列著,路易十四本人則是右手執權杖,左手置於懸掛著配劍的腰間,一臉輕鬆自在。這樣的圖像,是否就是路易十四加冕時的真實場景?傳統國王加冕圖像,莫不正襟危坐,顯示莊嚴肅穆的統治者氛圍,但畫家很可能曾看過Van
Dyck(1599-1641)為英國查理一世繪製的出外打獵肖像(Charles I of England at the Hunt),兩者的右手都拿著象徵國王權威的手杖,左手擺放位置與腰間配劍也如出一轍,亦即Hyacinthe
Rigaud將英國查理一世打獵肖像畫的構圖,轉化為路易十四的加冕情境,皇冠等皇室象徵物都在畫面中,但路易十四本人則呈現一種輕鬆拿著手杖,舉重若輕、泰然自若的王者形象。這些圖像內在的對話傳統是基於某些特定目的而被創造出來,進而被依循。而Hyacinthe
Rigaud這樣的表現方式,也成為爾後法國國王畫像依循的傳統,如路易十五、十六世都有相似風格的繪像。 有關圖像的隱喻,花教授則以美國南北戰爭期間(1861-1865)的畫作為例。當時主張解放黑奴的北軍穿藍色制服,主張蓄奴的南軍則是身著灰色軍裝,我們透過制服的顏色可瞭解此一時期畫作的重要隱喻。如Eastman
Johnson(1824-1906)的畫作The Lord Is My Shepherd,此畫的標題出自《聖經.詩篇》第廿三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花教授認為,畫中閱讀《聖經》的黑人所翻的頁數應該不是位於中段的〈詩篇〉,而是聖經前幾章節的〈出埃及記〉。此外,於炭火堆前讀經的黑人身後有一件藍色的制服,應該是畫家隱喻其人參加北軍。從真實的歷史來看,南方黑奴加入北軍者為數不少,顯示黑人並不是等待北軍解放的被動角色,而是實際投身軍旅的參與者,〈出埃及記〉與北軍制服的隱喻,是為鼓勵黑人從軍,實際參與自我解放的運動。 花教授指出,圖像本身就是一種視覺的溝通,但為避免落人口實的直接明瞭,畫家以隱微間接的方式傳達意念,如Winslow
Homer(1836-1910)的早年畫作Near Andersonville。該圖繪於南北戰爭後一年(1966),畫面中一位黑人女孩站在門前,一旁則是穿著灰色軍裝的軍人,押送著手無寸鐵的藍色制服俘虜走過,顯示戰爭雖然大致上塵埃落定,但在南方仍有許多地方還有零星戰事,對於黑人而言,自由真的能成真嗎?畫家刻意在黑人女孩的身前繪製了兩條不同方向的路徑,意味著黑人抉擇時的徬徨與忐忑,也暗示南方的戰爭情況並不如想像中樂觀。不過畫家另繪有許多葫蘆狀的水瓢,深入瞭解的話,會發現水瓢具有特殊意涵,正因水瓢的形狀像北斗七星,可作為指北方的象徵物品,很可能是鼓勵黑人北往從軍的隱喻,也就是畫家透過圖像的隱喻,傳達鼓勵黑人追求自由的意涵,也把黑人面對時代不確定性的壓力傳遞出來。另一方面也藉由畫面描述南方軍情的殘酷,如著名的安德森維爾監獄(Andersonville)是南方邦聯軍隊的戰俘營,據統計4萬5000名北方聯邦囚犯中,約有近1萬3000人死於營養不良、飢餓、疾病與虐待,或許這就是畫面中身穿藍色制服俘虜的悲慘遭遇吧。 歷史研究如何幫助我們對圖像內涵獲得更深入認識?花教授認為,歷史被隱藏住的訊息,可透過更好的歷史閱讀加強對圖像資料的理解。圖像可以提供歷史研究更深入的思考,不會受制於傳統或主流的歷史書寫,使研究者有更多元、更細膩的體會。以16世紀下半葉畫家Pieter Bruegel the Elder(1525-1569)為例,其雖出身菁英家庭,卻對農民生活有生動的觀察,素有「農民畫家」之稱。他在晚年畫作Peasant
Wedding中描繪農民婚禮,表面看似喜慶,卻把當時農民的艱辛表露無遺,如畫面中送餐人是用廢棄門板發送餐點,吃的也僅是麥片粥,表現出婚禮的困乏、貧寒。Pieter
Bruegel另一幅作品The Peasant Dance中則描繪了民眾於教會活動的情景,他使用平視角,描繪大人帶著小孩快樂跳舞,有人親吻,有人快樂飲酒奏樂,表現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展示眾生相貌;與此同時的另一畫家Pieter
van der Borcht(1530-1608)描繪同一主題時,則更加片面化,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衝突,參加者大打出手、暴動的景象,另外還有文字說明:「這些醉人打架鬧事,醉得跟動物一樣,去的人都是不像話的人,要去就去吧!」顯得負面許多。Pieter
Bruegel對於百姓傳統的生活,雖然於畫面中也展現了緊張的社會關係、衛道人士的不屑眼神,但始終不以批判的角度予以醜化,而是以人文關懷的態度,將這些活動視作困頓、貧乏農民的抒發管道。過往農民的生活如何,史料未必有特別記載,但透過圖像資料,研究者可從中發覺不同的訊息與觀察。 花教授最後提到,隨著交通工具與溝通媒體日益發達,世界相互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被複雜的網絡串聯,除了刻意造成的壁壘外,對歷史的解析越來越不能由意識形態的分類著手,得用更寬闊的角度看東西的文化,千萬不要被刻板印象宰制。從單一的角度去認知不同族群的交會,卻忽略地緣政治、利害競合、文化交融,往往是讓簡化的片面認知加深了誤解,如此作法非但不能使歷史學走向引領獨立思考之路,反而會陷入認知迷障中。因此,花教授認為「去標籤化」是現代史學家應該努力的方向,也是臺灣民主政治多元發展的重要功課。其實不管是學術跨領域研究,或面對正在民主深化的社會,謙卑耐心、互相對話是必須的,而對話就是需要時間與耐心。花教授最後鼓勵現場聽眾,在現今世界愈加錯綜複雜的情境下,更須重視培養解決複雜問題的創新學術能力,而走進學問道路的初心,就是要為這個世界帶來光亮。因此我們應懷抱著常常省思的心,走出舒適圈,去與不同思想的人們對話。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2卷1期,頁101-107。 |
||
|
|
指導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協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聯絡電話:(05) 310-6273 電子郵件:mostsalon@gmail.com 地 址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