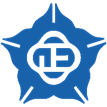|
第30場 |
||
|
日期:2019-12-13 講者姓名:廖咸浩 單位職稱: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主持人 | 陳明印(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地點 |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紅樓夢為何夢紅樓?
本次講座邀請廖咸浩教授以「紅樓夢為何夢紅樓」為題,分享其30年來研究《紅樓夢》的成果。講座初始,廖教授談及自己研究《紅樓夢》,甫於就讀史丹佛大學博士班的期末報告,當時未從政治角度切入討論,但已發覺《紅樓夢》比想像中來得複雜,多年後討論《紅樓夢》中南、北方的地域問題時,認為《紅樓夢》中諸多難題若由政治意涵著手便可迎刃而解,進而展開一連串系統性的研究。廖教授認為文學作品本就是個謎,《紅樓夢》尤為如此。《紅樓夢》書中謎語遍佈,諸如:人物的名字使用雙關(如霍啟諧音「禍起」,此人為甄家家僕,於故事初始即丟失書中第一位女角「英蓮」;薛寶釵之名可諧音並拆字為「保又金」,又金即後金,指滿清政權,「保又金」意味附清之知識份子),或以詩謎影射人物命運,或在節日的名稱與日期上有所暗喻(如芒種節餞花會、遮天大王聖誕同樣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種」與「餞花」應是暗示國種將亡與花神之死,為明朝國種、國魂之象徵;遮天大王屬虛構神祇,暗指「一手遮天」的滿清政權)。正因《紅樓夢》中大量費解的謎題,廖教授認為作者之寫作策略為「欲張彌蓋、欲語還休」,僅以草蛇灰線般隱約可尋的線索和跡象,供讀者玩味與檢視。 廖教授指出,閱讀文學必須探究其隱喻層面的意義,避免落入顧此失彼、如讀後感般表層的理解,以進行可貫穿整體的詮釋,方能趨近作者意欲表達的核心意旨,同時也應注意文學作品生產條件的重現,放回到歷史框架,探究寫作的環境,亦即作品如何反應社會及與社會的互動。歷來對於《紅樓夢》的詮釋有不同的路線,如1915年蔡元培(1868-1940)撰寫《石頭記索隱》,推論書中人物影射清初歷史人物,故此路線被稱作「索隱派」。大體而言,此派認為書中影射世祖順治(1638-1661)與董鄂妃(1639-1660,民間或將其比附為明末名妓董小婉(1623-1651),或認為暗指康熙(1654-1722)時朝中政治狀態及宮廷鬥爭,或認為指納蘭性德(1655-1685)家族興衰史,不一而足。1970年代索隱派一度於台灣復興,以潘重規(1908-2003)為代表,此時轉以強調全書旨在反清復明或排滿興漢之民族寄託。1921年胡適(1891-1962)〈紅樓夢考証〉一文為「考證派」開山之作,此文考證《紅樓夢》為曹雪芹(1715-1763)之作,書中所寫乃其親歷之家族史,故具有自傳性質,此說蔚為學界大宗。因胡氏影響,不少學者集中研究曹雪芹之家世,用以說明《紅樓夢》的情節,周汝昌(1918-2012)之《紅樓夢新證》為集大成之作,可說紅學已成「曹學」,也引來學人認為失卻小說之所以為小說的批判。1981年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則由純文學的角度,認為《紅樓夢》作為歷史與虛構小說的雙重面向,自有其體系與規範,實不需於索隱或考證間鑽牛角尖。1954年起,部分中國學者認為《紅樓夢》並非自傳,而是「深刻反應了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實已脫離文學研究的範疇,轉為馬克思理論在紅學研究上的借題發揮。 廖教授則認為現行對《紅樓夢》所謂「文學」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極力迴避書中的政治面向,除少數仍由階級鬥爭或宮廷內鬥的角度外,對於國族認同的遺民情懷多所排斥,這無非源於胡適對早期索隱派的沈重駁斥。當胡氏考證出《紅樓夢》作者為曹雪芹後,其生平與家世背景的挖掘,加深了學者對其國族認同的既定印象,特別是其家族為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侍於皇帝、宗室王公之家的包衣身份,似乎也意味他不可能有任何遺民情懷。而廖教授對於曹雪芹為《紅樓夢》作者的「定論」仍有保留,卻對書中俯拾即是的遺民情懷感到興味盎然,遂由比較文學與現當代西學理論的學術背景,將全書具備細膩結構的遺民密碼逐一解讀,自通篇各種雙關語、謎語或婉轉指涉,參透小說中的托寓,最終發展為個人獨特的詮釋體系。 廖教授指出,《紅樓夢》採以類似後設小說的故事架構,在先後兩種不同神話架構下展開,文本初始以女媧煉石補天神話架構展開敘事(可稱為「大荒敘事」),而由空空道人抄自未能補天頑石之上所記,則是第二層次的敘事開端(可稱作「太虛敘事」),內層則是大觀園及以賈寶玉為中心的情節(可稱「大觀敘事」),其關係為內層反抗中層,中層批判內層,外層批判中層,但也開示並同情內層。如第五回中太虛幻境之警幻仙子勸誡寶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將謹勤有用的工夫,置身於經濟之道。」(一本作「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太虛幻境代表著要求遺民(即寶玉所代表的遺民意涵)出仕清廷,而寶玉在大觀園內則以「情之為物」(對前朝之情,拒絕接受朝代更迭)作為唯一的生意意義,反應於「大觀敘事」則是寶玉厭惡讀書科舉,在警幻仙子予以規訓之後,反而遁入大觀園,此後對程朱八股、考試致仕的不滿更是溢於言表。 對於這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廖教授認為必須考量《紅樓夢》的「生產條件」(conditions
of production),挖掘其政治面向。基於蔡元培、潘重規等人的研究,廖教授以後殖民理論為基礎,提出以「國族寓言」的關照討論國族鬥爭論,認為作者是以外層「大荒敘事」的態度,批判中層「太虛敘事」所隱喻的清廷籠絡政策。警幻仙子之「警幻」一詞,可對偶於清朝雍正帝(1678-1735)親自頒行之《大義覺迷錄》一書之「覺迷」。清初文士曾靜(1679-1735)及其門人張熙(生卒不明)因不滿滿人統治,以呂留良(1629-1683)華夷之辨為思想基礎,陳列雍正帝的十大罪狀,認為其得位不正,並試圖遊說當時謠傳為岳飛(1103-1142)後裔的川陝總督岳鍾琪(1686-1754)起兵反清,岳氏假意應允,後逮捕二人押送京師,後雍正赦免曾、張二人,並下令收錄此案之有關文書,輯成《大義覺迷錄》。書中對曾、張二人所質疑滿族統治中國的合理性提出辯駁,認為當從文化角度提出新的華夷觀,而非傳統之服飾與地域觀。所謂「大義」即是接受滿漢融合、接受此朝代更替的歷史轉變乃「天命轉移」,接受清朝用以證明自身乃「新中華道統」的方法,就是自詡是清新版的程朱八股。廖教授以《紅樓夢》書中警幻仙子所代表的程朱理學言論為證,警幻仙子視寶玉之情為「意淫」,即指涉悼念明代之情,用以對立賈府代表的「皮膚淫濫」,實指明末心學興盛之情(當時檢討明代覆滅,原因之一歸咎於晚明的心學)。而外層的「大荒敘事」則以「偶然論」否定世變乃「天命轉移」,代表著作者立場,既批判中層的納編企圖,也為遺民情懷找到另一出口。廖教授認為雍正/警幻的論述頗近似當代後殖民理論,從根本上動搖當時的國族主義論述,故遺民便從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往文化民族主義做調整,從「保國」觀念挪移至保中華文化正統性的「保天下」觀念。 在人物方面,廖教授認為林黛玉、妙玉、薛寶釵、史湘雲四位大觀園中最重要的女性,代表了寶玉/遺民的兩種不同選擇:一為拒仕,一為編納。妙玉的避世逃禪與湘雲的見機行事,黛玉的出世傾向與寶釵的入世勸說,反應兩者所代表的不同意識型態,也形成明/清的對照組,在《紅樓夢》中,寶玉/遺民雖較傾向於前者,但亦不時受到後者影響。對於當代知識份子而言,讀書以求取功名是建功立業的根本,也是作為一「男人」證明自我的管道,而大觀園中的寶玉拒絕科舉的舉措,實則意味「不長大」與遺民的堅持。廖教授談及史湘雲是書中最壞的人物,從其名稱上可諧音為「使相云」,意指清廷新秩序的代言者。第二十一回中,湘雲幫寶玉梳頭,寶玉見「鏡台兩邊俱是妝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因又怕史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一手掠著辮子,便伸手來「啪」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才改過!』」,寶玉愛食胭脂的特性,前輩學人已多有論述,乃以胭脂之朱紅色暗指明朝國姓朱,而湘雲打落寶玉手中胭脂的舉止,則意味阻斷遺民思念舊朝的意念。廖教授強調其所稱「遺民情懷」不單指遺民本身,也包含排滿興漢的情緒。廖教授認為,薛寶釵的堂妹薛寶琴(諧音「保情」,保守明代之情)可能是作者在大觀園中的代言者,此可從其對史湘雲於大觀園中吃鹿肉(祿)帶來腥膻不以為然得見,作者也借寶琴之口道出南方之極有一「真真國」,國中有一披金髮、配倭刀、會講五經、作詩填詞的少女。廖教授認為這是作者對於臺灣的想像,「金髮」意味臺灣曾經荷蘭、西班牙統治,「配倭刀」則似指具有日本血統的鄭成功(1624-1662)。其次,寶琴誦出此位少女所作之詩:「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字裡行間似指南明最後的希望,即棲身於臺灣島上的鄭氏政權。 廖教授根據小說中的「草蛇灰線」,認為《紅樓夢》基本上是一部影射南明從力圖再造到無力接續,最終崩毀瓦解的歷程,作者經由賈寶玉的經歷,透過三層敘事的建立,表示「遺民情懷」的出口與轉變。書中男性所隱喻的是已為清廷納編的知識分子;女性則多暗指效忠、憶念前朝的知識分子。廖教授認為,作者最終以蔣玉函與花襲人的婚配隱喻了遺民的最終選擇。賈寶玉與蔣玉函交換私密的汗巾子,完成身分交換。蔣玉函為男扮女裝的乾旦,「不男不女,既男又女」,有如無法科舉致仕而成為「真男人」的遺民。而襲人原為寶玉的貼身丫鬟,故掙扎猶豫是否「事二主」嫁予蔣玉函,在發現蔣玉函實為寶玉的化身後,「事二主」的問題得以解決。廖教授指出蔣玉函之名意味「將(蔣)玉(明之國魂)放入函中」,與襲人的結合則是包裹「龍衣」暫離江湖,隱入尋常人家。而寶玉則剃度為僧、歸向大荒,意味著對於警幻的論述(歸順清廷統治)所做出的反抗,回歸滿人統治的、意義已然荒蕪的現實世界(大荒山的青埂峰下)。整體而言,廖教授關心的不是「遺民情懷」本身,而是政治的變遷與文化的回應,及書中透過文學書寫,將「甄士(真事)隱去,賈雨(假語)村言」,以文字隱語加密、虛構,擺脫文字獄與對抗攏絡、納編,廖教授藉由挖掘《紅樓夢》的深層意涵,重新評估其藝術價值,也從後殖民的角度思考文學研究的當代意義。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1卷2期,頁106-110。 |
||
|
|
指導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協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聯絡電話:(05) 310-6273 電子郵件:mostsalon@gmail.com 地 址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