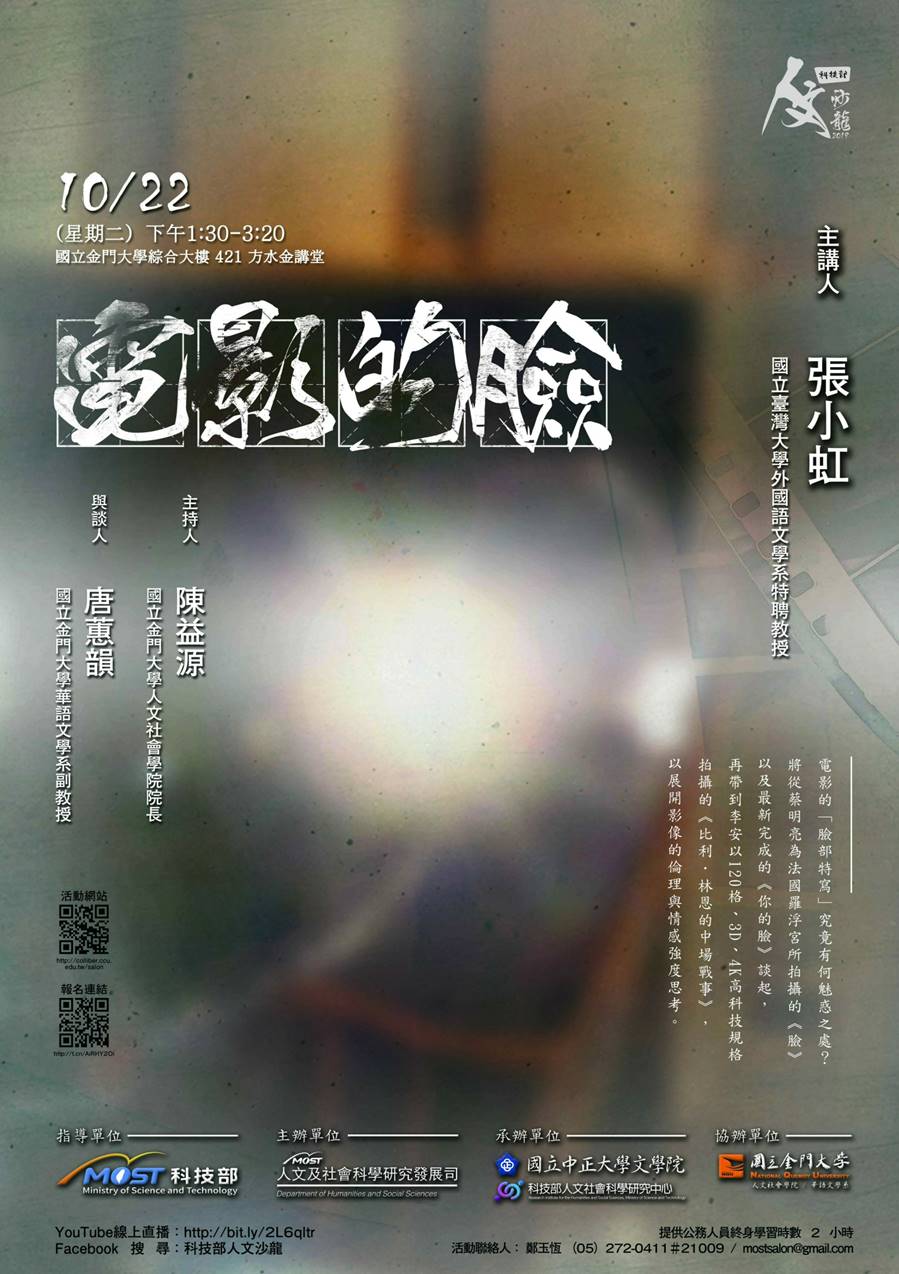|
第28場 |
||
|
日期:2019-10-22 講者姓名:張小虹 單位職稱: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主持人 | 陳益源(國立金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與談人 | 唐蕙韻(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地點 | 國立金門大學方水金講堂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電影的臉
對現代人而言,電影是極普遍的視聽藝術,也是生活娛樂的重要來源。不論是走進電影院,抑或以各式各樣螢幕觀賞,人們在閒暇時間馳騁於電影的天地中,電影儼然成為現代人繁忙生活的心靈綠洲。電影創始於一百多年前,從無聲黑白的短片,發展到如今運用電腦合成影像製作特效,打造奇幻非凡的數位效果,可說電影讓世界以一個嶄新的方式與面貌向世人展示,改變了人們觀看世界的角度。本次人文沙龍講座主講人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張小虹特聘教授,除了長年關注女性主義、性別研究、文化研究等,對於影像探索、國家結構與個人間的權力及情感關係,都有深厚的研究成果,她也曾多次主持科技部研究計畫,探討影像中的思考翻轉與美學感受,可說是一位橫跨影像、性別、文學三大領域的專家。在本次講座中,張教授由電影歷史發展與理論的脈絡出發,剖析兩位知名台灣導演蔡明亮的作品《臉》、《你的臉》及李安《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進行影像的倫理與情感思考,由「臉部特寫」探索電影的底蘊。 張教授指出,萬事萬物都可以有「臉」,電影的「臉」基本上就是指電影本身,電影使任何事物轉變成一個敏感可讀的表面,就是一種「臉」。1895年底時,法國盧米埃兄弟在巴黎卡普幸路的一家咖啡館地下室,首次公開放映他們拍攝的短片,這部片長僅有五十秒的黑白無聲影像,紀錄了蒸汽火車牽引著客車,從遠景漸漸駛入拉西奧塔(la
Ciotat)車站,據說這段「火車進站」影片令當時眾多觀眾受到過度驚嚇,奪門而逃。張教授指出,這則故事的真實性猶有討論空間,有人認為是因為地下室空氣稀薄,造成很大的情緒壓力;也有人認為是因為不久前發生火車出軌撞上房子的事故,使人們餘悸猶存。但若從討論電影的初始階段來看,此頗具戲劇性的場景正可說明,電影的誕生帶給當時人們莫大的視覺衝擊,因為畫面的真實感,讓人感覺火車就要撞過來了。電影作為新事物,帶給當時人們驚嚇、驚奇,同時也是充滿魅力、誘惑力,但如今電影發展已逾百年,在資訊發達、3C設備便利的現代,人們已不見得透過大螢幕觀賞電影,則電影仍有炫人耳目的魔力嗎?於是張教授由電影史、電影理論怎麼看臉部特寫,討論電影帶給人們的情感與意義。 由於早期電影都是默片,並無對話,故此一時期也是對於臉部特寫的討論高峰期。匈牙利電影理論家巴拉茲(Balázs Béla,1884-1949)便特別關注默片電影的臉部特寫,他認為,電影將人們從真實事件的慣有感知中抽離,以此開啟嶄新的視覺經驗,尤其是電影特寫的「顯微」功能,可特寫放大事物,將隱而不顯的面貌賦予獨特生動的畫面。巴拉茲同時也是一位實踐創作的導演,對於大自然、都市、人物乃至於機械,都特別凸顯面相,他的電影詩學正是將世界「樣貌化」,在觀看電影的同時,也彷彿觀看世界變化萬千的面相。張教授提到,巴拉茲對默片電影臉部特寫最知名的表述,莫過於「微面相學的無聲獨白」一語,「微」象徵某一種敏感度、不確定的世界,正因為電影變化了事物原有比例,更能凸顯微小的變化。而電影與攝影、繪畫不同之處,即在於電影能呈現動作變化,這種變化便象徵了時間。演員或角色透過臉部表情做出無聲的獨白,這種「獨白」是說給眼睛聽的,因此更具抒情效果與情感強度。巴拉茲相信,臉是靈魂的反射,比語言坦白與大膽,更傾向於人的本能及潛意義,亦即,巴拉茲的電影理論更強調臉的「內在性」與「精神性」。 另一位電影理論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本身並無電影創作,但在其〈電影小史〉文中提出了「匿名面相」一詞。班雅明此語乃是針對十九世紀中葉蓬勃發展的人物肖像商業攝影,在當時,「肖像」所呈現的重點是被攝影者的人格特質與社經地位,從攝影處的背景裝飾中也可見其品味,亦即是具備濃厚的階級意味。而電影鏡頭前的「匿名面相」,卻能讓人臉展開劃時代的嶄新意義,跳脫商業價值與身份地位的限制,以平民大眾取代達官貴人、英雄豪傑,頗具有「革命」的能量。班雅明在其名作〈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更進一步強調電影如火藥般的動能,將肉眼所見如監獄般的真實世界炸裂開來,透過特寫將空間延展,經由慢動作將運動延展。對班雅明而言,電影中的面相能透過攝影機的放大與形構,將藏匿於微小事物中的細節彰顯。面相凸顯的不是內在深度,而是「表層價值」,亦即人體與世界接觸的敏感表層。張教授指出,班雅明對於攝影機「顯微」功能的強調,與巴拉茲十分相似,他認為攝影機的電眼不僅能顯微至肉眼無法瞥見的面相,更能將此面相以全新的主體形構方式呈現。因此當班雅明談論面相的特寫貼近時,由體感的「近」拉到空間影像辯證上的「遠」,也說明了電影打破了人們觀看世界的方式。 張教授談到,因為體感上的「近」,法國導演暨理論家艾普斯坦(Jean
Epstein,1897-1953)一方面強調視覺,認為特寫為「極大化的視覺敏感度」,並將電影視為心智(psychic)活動、一種形式理念之重要,另一方面也凸顯特寫所造成「現象世界的感官毗鄰性」,讓影像的體感空間變得敏感貼近。而艾普斯坦尤為強調電影影像與觀影觀眾之間的敏感貼近,觀眾透過攝影機,以特寫的方式親密貼近,悠遊於多重感官的面相世界,這樣的敏感貼近,甚至可讓銀幕上的痛苦情感變得觸手可及。因此,艾普斯坦認為,電影是情境,是感官瞬間形式的情感強度,可流洩於電影院做為另一個情境的體感空間,與觀眾做為另一個體感空間中接觸傳染的對象。 張教授以1928年黑白默片《聖女貞德蒙難記》為例,當時以全色膠片技術拍攝,這種膠片能讓黑白片的景觀變得自然,也能自然地紀錄皮膚的顏色,遂使得本片所特寫女主角的臉孔,成為默片史上的經典畫面;導演李安2016年的作品《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則是120格、3D、4K高科技規格進行拍攝,與《聖女貞德蒙難記》每秒16格的規格判若雲泥,以如此高規格、高幀只是為了「顯微」細節?抑或為了避免過去24格、3D規格時,演員臉上出現動態模糊嗎?張教授指出,李安拍攝《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是以最高規格影像來改寫時間的定義,並透過各種敘事構築來組成反戰的思維(如戰場與球場、砲火與煙火的交叉剪接),但李安高明之處在於將高科技所能帶給觀眾最直接的影像情動力(affect),將關於科技、哲學的詰問,翻轉為關於影像倫理的思考。張教授舉例,美國911事件中紐約雙子星大樓的崩毀宛若好萊塢災難片,IS則向全世界推播斬首人質的血腥影片,日前美國總統川普更以興奮而輕蔑的口吻說道「就像看電影」,述說美軍殲滅行動衛星直播畫面的身歷其境。正因現代「戰爭影像」的真實或超真實已不再可能,而使用演員、道具、敘事、場景來拍戰爭電影還能有未來可言嗎?李安導演卻是用最高規格的影像來特寫死亡,透過角色眼中的血絲與恐懼,使觀眾凝視死亡,也被死亡凝視,提醒著每個死去的人都曾是活生生的人,以影像本身的高幀來反戰。 張教授另談及蔡明亮2009年的劇情長片《臉》,本片為法國羅浮宮規劃拍攝並典藏的第一部電影作品,其運用羅浮宮的達文西畫作《施洗者聖約翰》為素材,將其背後的聖經故事編寫為劇本。2017年,HTC出資邀請蔡明亮拍攝了號稱第一部華語VR電影《家在蘭若寺》,然而對蔡明亮而言,VR剝奪了導演想給觀眾看什麼的掌握權,亦即無法讓觀眾只凝視一張臉,於是隔年2018年蔡導演完成《你的臉》,這部作品既非劇情片亦非紀錄片,而是以13張被歲月刻畫的臉部特寫組成。張教授由自身觀看這部作品的經驗指出,在這些臉孔被蔡導演規定只能默坐25分鐘的時候,臉孔被攝影機凝視,而觀眾再藉由攝影機凝視這些臉孔,這其中就有「凝視」本身的倫理性問題。片名強調「你的臉」就呈現一種「你/我」的倫理關係,同時「你的臉」在某種意義上也不會是「你的」,因為人是無法直接看到自己的臉孔,因此人的臉孔也往往是他人觀看的對象。透過《你的臉》,張教授也思考電影的臉究竟是用來「敘事」或「蓄勢」,所謂的「蓄勢」指蘊含著一種情感的能量,亦即班雅明指稱之「表層價值」。從蔡明亮的VR電影之作,彷彿是預告舊電影的死亡,然而從《你的臉》又似回歸電影的前期,如此強烈的臉的造型出現在21世紀,意味著透過新科技去追溯古老的電影時代。電影的發明,讓人們得以透過電影的眼睛,重新觀看我們的世界,讓我們用一種新鮮的感覺去感受這個世界,這曾是電影被認為最具革命性的地方。而李安與蔡明亮則用現代科技,再度以電影的臉部特寫,為我們展現21世紀電影影像的可能與不可能,同時也是對於「電影是什麼」及「電影還能做什麼」所提出的嘗試與解答。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1卷1期,頁148-152。 |
||
|
|
指導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協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聯絡電話:(05) 310-6273 電子郵件:mostsalon@gmail.com 地 址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
|